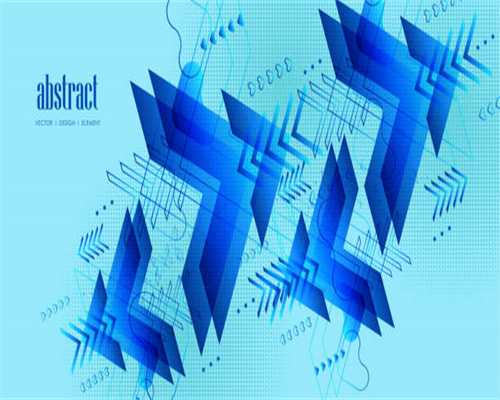1
老师在讲台逼逼个没完,我下面的小水库汹涌澎湃,水不停上升,一点点逼近坝顶,我迅速加固加高大坝,可惜我加高的速度远远低于水面上升的速度。
溃坝的瞬间,在同学们不可思议的眼光和老师有点痴傻的表情中,我像一头捕食中的豹子,迅捷又粗暴地蹿出了教室。
那是我一生中最最牛逼的时刻,大胆、狂野、孤傲,不讲任何狗屁规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我冲出教室,冲过操场,再转过一堵墙就是我现在的所有、一切——厕所!
转过墙,麻蛋!上节课还在的厕所消失了,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打麦场,一大群男男女女在里面忙碌着。
虽说自己在他们眼中是个标准的小屁孩,但,再怎么说我也是学前班的大同学,说啥也做不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脱掉裤子拿出小鸡鸡放水。
还好,打麦场边有几个高大的如同堡垒一样的麦秸垛,这时候我已处于忍无可忍的边缘,随时有尿裤子的危险。几步跑到麦秸垛后,在我即将酣畅淋漓时,耳朵里出现单调的“唰唰”声,那声音从清晰到模糊,又从模糊回到清晰。
挣扎中我睁开了眼,“唰唰”声越发清晰,我猛得一激灵,秒速跳下床,撒丫子往厕所跑,激荡的尿柱喷射而出后,我一身舒畅,那感觉堪比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你,激奋而飘飘然。
从厕所出来,这才注意到,门楣昏黄小灯泡的光影下,老爸蹲在一个大磨刀石前“唰唰”地磨着镰刀,嘴里叼着的香烟闪着暗红的光。
老爸磨一会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滑过,这是试刀刃的锋利程度。他身边放着五六把磨好的镰刀,别误会,我们家没那么多割麦子的大劳力,这些镰刀都是老爸老妈俩人用。
N多N多年前,蒙古铁骑远途奔袭时每个骑兵会配备两到三匹战马,途中不停换骑,以提高行军速度。老爸肯定没见过那些骑兵,更不会跟他们喝酒聊天儿,从而在他们战马身上得到启发。
但老爸从长期劳动中知道,一把镰刀是坚持不了多大会儿的。
再锋利的镰刀割不了多少麦子也会变钝,用钝镰刀割麦子能累死你,用蛮劲后往往会把连着干燥泥土的麦根一块扯出来,这样的镰刀用一上午,再壮的汉子也会废掉。
老爸看我一眼,挥手叫我进屋,那个时候天儿还没亮,应该有四点多钟,我上了床,迷迷糊糊又着了。再次醒来已是七点多,锅里留有老妈熬的粥,不过早没一丁点的热乎气,他们早就吃过割麦子去了,要一直割到快晌午才能回家。
歇晌到三点多钟,老爸重新把上午用钝的镰刀磨快,带上一大壶水,继续下地割麦。三点多的太阳正是傲骄地不讲道理的时候,细皮白肉的城里人太阳地儿站一会儿估计能晒脱一层皮。那也得去,麦子是你自己的,不去没人管你,不抓紧收,一场大雨全得烂地里!
吃饭?吃个锤子!
所以,太阳再大,再烈,也抵挡不住乡亲们下地割麦的“热情”。我爸妈三点多去算是正常钟点儿,有的人不到两点就下地了!那才是牛逼的钢铁战士。
2
一个壮劳力起早贪黑地干,一天大概能割一亩的麦子。个别极彪悍的能割个一亩二三,再多是会出人命的,彪悍的人终究也还是人,而不是机器。
我割过几年麦子,说实话,那滋味不好受。天不亮开干,那会儿麦子上全是露水,摸着潮乎乎,不幸的是我的皮肤对麦子上的露水过敏,长时间接触后身上布满皮疹,那东西能把你痒死!所以我割麦子前得把自个儿包裹得严严实实,装备穿齐全后相当于一个低配版的木乃伊。
因为穿得严实,干一会儿,浑身湿透,憋得想窒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最不能忍受的是腰,我那没干过重体力活的小嫩腰在长时间弯腰撅臀持久劳作下很快崩溃。
先是酸,接着麻木,很快变成疼,最后失去知觉,好像腰子不再属于自己。而且干到一定程度不仅仅是腰疼,胳膊、手、大腿、小腿全疼,尤其是手慢慢麻胀地握不住镰把。想着都累成这样了,应该快割到头了吧!
抬头,操!连一半都没有。老爸、老妈、哥全在我前头。咬咬牙提速,操着镰刀不管不问只是乱割,结果小腿一凉,完蛋!别看镰刀割起麦子笨得要死,割肉那叫一个快,轻轻一下,腿上血流不止,疼得我嗷嗷直叫。
那年我上初中,可能兄弟们要说,你是小孩,肯定不行,大人就没问题。
大人?壮劳力割一晌麦子,腰子照样废!
我们村流传一个段子。一哥们割了一上午的麦子,腰硬得不会打弯,这哥们一进屋就嚷嚷:“坏了,坏了,又硬了!”
他媳妇正在揉面,白他一眼:“睢你那点出息,再硬也得等我洗洗手吧?”
还好,我们村人均亩把地,咬咬牙,割个两三天也就完了。接下来的任务是拉麦子,听说以前是用架子车人力拉。割完麦子基本上累个半死,接着纯人工拉几亩地的小麦,那感觉······
还好,现在拉麦子的活是骡子干的。
骡子苦呀,自己出身不明不白,偶尔想在爸妈跟前撒个娇吧,还不知道自己爹娘是谁,想找都没得找。又得一辈子给人类当苦力,悲催的是它们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后代!
当你感觉自己苦逼的不如去死时,想一想骡子,比起它们,你大概能理解啥子叫幸福。
骡子车是本家一大爷的,割完麦子后,拉、打要一个家族合作,自己单独是干不了的。整个大家族的小麦拉完后,每家给这个大爷若干斤饲料,不能白嫖人家的骡子不是?
几年后,我们家买了台拖拉机跑运输,麦收季拖拉机替代了骡子的活儿,骡子终于解放了,以前难熬的麦收季现在成了它的休闲假日。
麦子集中拉到一个叫打麦场的地方。
打麦场其他季节也种小麦啥的,麦收前这块地的作物要提前收,然后平整土地,接着无数人提着水桶,一桶一桶把打麦场全部泼湿,再把上年的麦糠洒到上面,接着拖拉机拖着大石磙将混合了麦糠的土地碾压瓷实。这个过程叫“操”场,嘿嘿,“操”场,这名儿起得多少有点少儿不宜。
操完场,等太阳把地皮晒干晒透后,电工竖电线杆子拉电线,装超大瓦数的灯泡。
各家各户也没闲着,把自己家的大水缸啥的拉到打麦场,并盛满水。我们家拉的是一个叫“缸䓍”的玩意,它比普通水缸低一半,但肚子要大好几圈,好处是盛的水不比水缸少,个头还矮,打水很方便。
记忆中这些消防水缸从来没用过,刚开始缸里的水清澈透明,没几天变得浑浊,最后那水黑而臭,里头翻滚着无数活力四射不知道谁的后代的小虫子。
3
所有这一切做完后打麦场正式投入使用。于是麦子拉到打麦场开始脱粒。
小麦脱粒在中国几千年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先全部均匀摊开,太阳暴晒后用石磙碾。古代大概率用人拉石磙,还好,现在拉石磙得是各个生产小队的拖拉机,这大大减轻了劳动程度,否则先割再运,最后还要拉石磙,人不累死也得累吐血。
石磙碾过赶紧趁着热乎劲把碾掉了麦桔头的麦桔杆用木杈挑到一边,这活叫起场。
木杈又叫桑杈,这东西制作超级麻烦。从桑树苗起开始整理,接着是各种校正,成形收获后还得进一步上特制火炕煨烤,然后上专用工具进行各种弯曲与拉直,复杂程度不比酿造茅台酒简单。
木杈是收麦子的专用工具,离了它收不成麦子,再加上从桑树苗到桑杈最少得五年,又是纯手工生产(放现在,光一个纯手工就能吹一辈子,价格也会高到离谱。),产量不是太高,所以那玩意卖得不便宜。
不便宜也得买,离了它收不成麦子,好在木杈很耐用,只要不粗暴对待,一杆杈能传好几代,人走杈还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麦场上出现了铁杈,慢慢铁杈越来越多。铁杈好用且便宜,木杈眼见不妙,赶紧降价,这才稍微有点活力。
不出意外的话木杈早晚要被铁钗干掉,不过最后被干掉的除了木杈竟然还有铁杈!
在大步前进的时间面前,一切皆是渣。
起完场要把掺杂了麦粒和麦糠的混合物拢成大堆,接着架上大电风扇,用一把木锹对着电风扇一锹锹把麦粒跟麦糖高高抛起,用风扇将麦粒与麦糖分离,这个过程叫“扬场”。听说厉害的老把式是不屑于用电风扇的,只用一把木锹轻轻抛洒后就能得到干干净净的麦粒。
好,现在终于得到了干净的麦粒,赶紧把他们装进口袋(装过各种品牌化肥的蛇皮袋子),再运回家里,这是不是意味着麦收结束,丰收到了家?
错!现在的麦粒里还有不少水分,不抓紧暴晒是要发霉的,严重的会直接变成酒。
在哪晒麦子?拉到大街上行不行?
不行,那会的街道全是坑坑洼洼的烂路,遍布土块石子,这样的路面晒过麦子,一百斤变一百二!这麦子怎么吃?
于是家家户户都把小麦在房顶上晒,那会大家盖得都是平房,晒麦子那叫一个得劲儿。但上房大多靠木梯或者铁梯,不管哪种梯子在房沿架好后角度在七十到八十度之间,胆儿小或者恐高地上一次得尿一次裤子。
然而当时我们要扛着一整袋的麦子,一手拽紧袋子,一手抓着梯子上房,几亩地的麦子都是这样一袋一袋背到房顶,晒干再扛下来了。后来家里用砖和水泥修了真正的楼梯,再扛麦子上房,那感觉······
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传说中的幸福!
4
大概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田地出现了一台收割机,不对,不对,那只是一台小型的割麦机,只能将麦子割倒,之后一系列的活还得靠人干。
我们家没用过这种机器,不是嫌贵,实在是抢不到呀!方圆十几个村,只有这一台机器。
如果说现代大型收割机是少女的话,那台只能割倒麦子的机器就是一嫁过三十次最后死了男人的寡妇。就是这样一寡妇,也是相当的抢手,无他,周围全他娘的是五十大几的老光棍!
这样说吧,麦穗刚刚变黄就有人把割麦子的订金送给割麦机老板。等到正式开割,每天会有无数的人跟在机器后面,天天会为了下一家该轮到谁而吵架,遇到俩火气大的,一准会发生肢体冲突。
老板只要机器不坏,会从凌晨干到下一个凌晨!不好意思,有点夸张。但,他每天休息的时间肯定超不过四个钟头,每年半个月起步。
在麦收结果后,他变得黑、瘦、憔悴,这寡妇当得不容易呀!没办法,看在钱的份上,受吧。
两年后所谓的收割机在村里出现了。那是一台大50拖拉机(马力50匹,我们家的小四轮只有15匹。)加装了收割设备后的简易收割机,平时这台5O拖拉机还干耕地、运输的活儿,只在麦收季短时跟收割设备结合变身为收割机。
这种收割机没有装麦子的粮仓,在收割机一侧有一个出粮口,出粮口相对有两个铁椅子,坐俩儿人,一人屁股底下压一摞袋子。一人在出粮口接满小麦后推动铁把开关,短暂关闭出粮口,并飞快拖出袋子,另一个眼疾手快把手里的袋子套在出粮口,打开出粮口。
拖出袋子的人用绳子扎紧口袋后,一脚踹离,再从屁股下拿出袋子,这时候对面哥们袋子里的小麦也快满了,两个人就这样周而复始。几亩地收完,接麦子的俩人累个半死,乌黑地粉尘粘满汗湿的全身,活脱脱一新鲜出炉的煤窑工人。
但是,跟以前下地狱一样煎熬地麦收季相比,这活儿又简直幸福到了天堂。
于是机器成了村上最最受追捧的明星,比现在的小白脸戏子们强得不要太多太多。N多人带着干粮追机器,晚上还得带被子,睡在机器干活的地边,就怕别人加塞儿!一般追个四五天才能轮到给自己收麦子。
虽然这机器有麦茬高、漏麦籽的毛病,但,一点也不耽误人家当流量明星。
大概又过了两三年吧,村上终于出现了真正的收割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台绿色的机器,独立的粮仓上印着黄色的“新疆2号”。这机器比50拖拉机变身的收割机强了太多太多,除了不用人工装袋,收得还干净,速度也快。虽然价格贵了点,大家还是愿意用。
那台猴版的50拖拉收割机一下子受了冷落,没办法第二年它也加装了粮仓,不用人工辛苦装袋子,价格还便宜。这样勉强有一些生意,没几年,村里又有人买了两台收割机,加上过路麦客们的收割机,村民再没人用那台变形金刚一样的收割机。
最后那套被50拖拉机抛弃的收割机在村口孤零零生了几年铁锈后,终于被卖了废铁。
5
我那个有骡子的本家大爷是村上最后一个用上收割机的。不是他没钱,是他看不上收割机。
他有自己的道理。用人工收割不仅不用出收割费,还能卖麦秸!用收割机,收得没人工干净,又得给人家机器钱,一来一去,这得损失多少钱!
关键一点,机器得等,而且等起来没点,万一下大雨咋办?我用人工收,想啥时候收就啥时候收,即不要看人脸色,还不用害怕下雨。
那我为啥要用收割机?我傻了呀!
可惜,本家大爷只坚持了两年,然后就投降了,累!太累!还是用机器吧,这麦秸咱不卖了。多说一句,本家大爷是不嫌累的,奈何孩子们嫌,熬了两年,说啥也再不合作,万般无奈,大爷只能从了收割机。
小时候麦收结束后,打麦场上四边散布着无数高大的麦秸垛。到了冬天收麦秸的小四轮拖拉机装得像小山一样高,走过后,遗留一路的碎麦秸。
麦秸用来造一种黄色的草纸,这种纸基本上全用来做包装纸,包什么?
点心!
在生活贫困,物资匮乏的时代,黄草纸包裹着的各种点心,无疑是孩子们能流一地口水的好东西。
我脑子里一直存有一个画面。
我哥站在小凳子上,凳子下是椅子,椅子放在桌子上,哥的手伸入悬挂在房梁挂钩上的篮子里。抠摸半天,把篮子里点心包的黄草纸弄破一小角,从里面摸出一点心,先给我一块,再自己吃一个,最后拿一块留着,到没人地方哥俩分了吃。
我不敢上,每次,他上,我在外面放哨。记忆里从来没被发现过,当然也不会挨打。
印象里,以前收麦子都是在半夜,装完袋子运回家也两三点了。而且那时候麦子含有不少水分,要晒好几天才能要在某个下午把散发着小麦特殊味道的袋子扛到房里,塞上防虫子的药后,再严严实实的裹上几层塑料布,当然干完这一切,无一例外得出一身臭汗。
然后在冬天小麦价格最高的时候卖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麦不到干透绝不收割,收割机收过,直接放进奔马三轮车里,拉到村里水泥路上。村上的水泥路每天有专业的卫生队打扫,干净的能当灶台使,用来晒麦子那是大材小用。
麦子稍微一晾晒,就达到了入库标准,下午就会被下乡收麦子的买走。人家收麦子用得也是机械化装备,不再用人费力得往车子里扛了。以前他们下乡收麦子给得还是现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人家也用上了微信跟支付宝,手机一扫,人民币到手,不要太方便了。
收割机收过麦子后,地里会有无数的拾麦穗的。每次收过麦子后,我爸会着急忙慌的下地拾麦穗,生怕叫外人捡走。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很少再有人拾麦穗,老爸对掉落的麦穗连看也不带看。
一场大雨后,地里会长出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
6
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里头有“麦浪翻滚、银镰飞舞,农民伯伯喜收小麦”之类的描写,当时对这些文字没感觉。长大后经历了割麦“教育”后回想那些文字,心中默默蹦出两个字——“操蛋”。
这文章纯粹是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把他赶进翻滚的麦田,操起银镰飞舞一天,看他还有个屁的心情写。
初中老师有次很伤感的说:“解放都几十年了,农民还得拿着镰苦哈哈的干活,咱们太落后了!啥时候我们也能像美国那样?”
二十年后,我的家乡终于实现了耕作的全部机械化,虽然晚了点,但是我们还是赶上了漂亮国。
从刀耕火种到全部机械化,我们走了几千年,这一刻,终于实现了,啥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我闺女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干过农活,说她是一个农民,那是抬举了她。当然了,不仅她没下过地,比她大点或者小的也都没有。说她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一丁点也不冤枉。
大胆预测一下,大概用不了多久,农村的田地会实现集中耕种,田地交给某人或某个机构,委托他们耕种,年终分钱。
那个时候的农民还叫农民吗?
不敢想,今天的家乡,今天的中国发展太快,想象力贫乏的人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
但有一点,他们是会知道的,那就是日子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