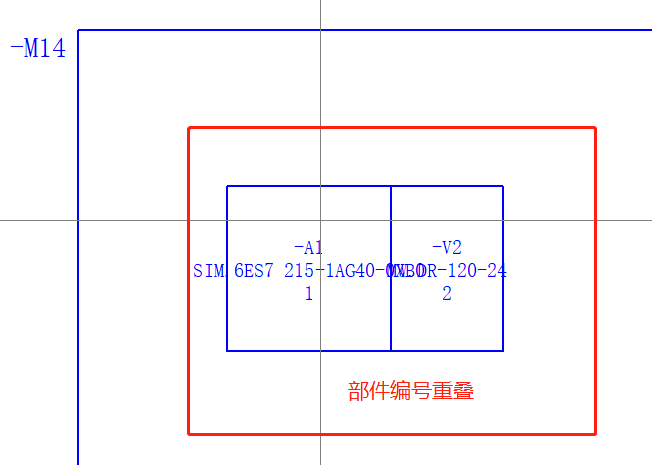不知道什么时候,麦子不再摊在麦场,而是铺满了大街小巷和水泥马路。
当联合收割机停满马路两边,不断有农民朋友和老板商量好价钱,跳上老板的车驶向自己家翻滚着黄色波浪的麦田,忙碌开始了。
田间地头、家家户户因为收麦而热闹起来,往往一大块地的几户人家商量好了以后,用同一家的联合收割机,自己备好口袋,最多一天功夫,伴着落山的夕阳,麦子会出现在家门口的水泥路面上。
见面问的最多的话语是,“麦子收了吗?”、“打算粜给谁?”、“你家的麦子卖了多少钱?”,收麦的程序一减再减,缩减到不需要打卖场的地步。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打麦场还是爷爷、父亲和自己三代人的记忆。
爷爷那代人根本没有看到过什么是打麦机,更不必说现在流行的联合收割机。那时候,打麦必须集中在麦场进行。
往往端午节前,爷爷已经用牛拉着石磙,石磙后边绑着密密的杨树枝条,从最里圈开始,绕着圆形的场子,“打、打……打”地吆喝着老黄牛一遍一遍地转圈,压平、夯实地面,如果让打麦场光滑如溜冰场,就需要选准一个下中雨后的时间,开始整理麦场。
当雨后的露珠被太阳晒干,刚碾压过的打麦场光滑似暗黄色泥鳅,紧实、细腻,在初夏的阳光下冒着缕缕热气,变得越发适合打麦、晒麦子了。
当空气中弥漫着麦香的时候,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镰刀、一大壶水的人们开始下田割麦,场景神似白居易《观刈麦》里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往往也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我们小孩子则在麦田附近的山坡上放牛,抽空再割些草带回家,一定要把家里的老黄牛养得膘肥体壮好有力气碾麦子。
和《观刈麦》不同的是,爷爷他们从地里拉回了一车一车金黄色的麦子,铺满了整个麦场,也把幸福的笑容铺满了古铜色的脸庞。
父亲赶着老黄牛开始拉着石磙吱吱呀呀地碾麦子了,爷爷、奶奶和妈妈在旁边不停的翻着麦子,我和哥哥姐姐一起,把从地里拾来的一小捆一小捆麦子放在麦场边上,用光溜溜的木棍一下一下地打出麦芒里包裹着的麦子……包括牛在内,都要赶在中午毒辣辣的太阳之前忙碌着。
偶尔,我喜欢在碾好的麦秸上翻两个跟头。奇怪,他们并不恼,反而笑呵呵的数我一连翻了几下,我在他们的笑声中翻得更起劲了,顺翻、倒翻、侧翻,如同猴子……往往头上、衣服上沾满了麦杆和已经瘪了的麦穗。
一场麦子辗得差不多了,我赶牛去麦场附近的山上吃草。爷爷和父亲开始了用叉子挑开麦子,堆成一个圆圆的麦秸垛,再把撵好的并不纯净的麦子扫成一堆。
爷爷和父亲往往喜欢在这时点起一支烟,一屁股坐在麦场边,目光望着悠远的蓝天白云,眉头紧皱。
原来是树叶一动也不动……突然,树梢动起来了,风大起来了,鼓起了爷爷穿的长袖上衣,父亲的衣服像张起的帆,他们爷俩不约而同的舒展了眉头,起身扬场。
我喜欢目光追随着他们铲起的麦子,看着他们高高扬起木锨,麦皮子像头皮屑一样飘到远处,落到麦堆上的基本都是干净的麦子了。如果有不干净的麦穗或者麦皮子,眼疾手快的母亲往往会用大扫帚轻轻从麦堆上一划一划,把颗粒饱满的麦穗又集中到了一起,哥哥、姐姐则用又直又光滑的木棍不断地敲打着母亲扫到麦场边上的麦穗。
我还喜欢在看牛吃草的同时,也来凑扬场、打麦子的热闹,但往往要被爷爷和父亲他们“轰走”。
当太阳挂在天空的正中,我家的麦子已经扬好摊开了。绑好牛的我最喜欢赤脚摊麦子,痒痒的、滑滑的、光光的,好不惬意。
这时候,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是“卖冰糕了,又甜又解渴的老冰棍了!”。远远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个用棉褥子盖着的白色小木箱,我们都知道是卖冰糕的人来了,赶紧又是挥舞手臂又是用两手做成喇叭型大喊着。
“买冰糕!我们这儿买冰糕!”爷爷往往会在我们的呼喊声中,从他的旧长裤里掏出一个手绢,拿出里边卷着的一叠钱。
我们兄妹三人是舍不得大口吃用白糖做成的冰糕的,个个伸出小舌头慢慢地舔着吃,直到舔出了最里边扁棍子,还要意犹未尽的把已经不再有甜味的冰糕棍含嘴里许久。
只是我们兄妹三个吃冰糕,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都是不吃的。他们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吃着当时最美味的东西,连说着自己吃不了那东西,一边“喜欢”大口喝着凉开水。
不断地割麦子、装满车,运到打麦场,晒麦子、碾麦子,再到扬场、晒麦子……忙过了端午节,忙到了七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爷爷他们的脊背似乎弯成了月牙。
我们小孩子在大人回去吃饭时,往往要在打麦场上疯玩一会,捉迷藏、警察抓坏人……玩累了,有时都在麦秸垛旁边甜甜地睡着了。
最害怕的是下雨,看到没有星星的夜晚,爷爷和父亲会用一张大大的塑料纸蒙好麦子,塑料纸边上用石头或者拉麦子所用的压杆围上一圈,以防风刮开麦堆。
当晒麦子时,发现西边出现黑云,风也越刮越大时,一家大小要齐上阵,和即将来临的大雨赛跑,开始拯救麦子了。
锨、扫帚、簸箕等都排上了用场,铲、扫,往布袋里装……
当装好后的麦子,用塑料纸盖好,一场大雨来临了。有时,来不及收的麦子会被大雨冲走……天晴以后,场边往往会出一层层绿绿的小麦苗。
大雨来临前,看到谁家的麦子没有收好,爷爷和父亲他们会经常跑到别人家的麦场帮忙。
直到麦子晒干,一袋袋运回了家。家家户户的打麦场里出现了好多个下圆上尖的麦秸垛,麦收才告一段落。有经验的爷爷往往能够根据麦稭垛的大小和数量,推算出这一人家今年的麦子收成,误差最多不会超过两袋麦子。
“神了!”正在吸着旱烟袋的爷爷一边接受着赞扬,一边和喜获丰收的老爷爷开始在石板上拉起了家常。
这时候的打麦场恢复了暂时的宁静,暑假以后,豆子和玉米等又会连同收获的喜悦集中到这里。
刚才讲的故事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黄牛、架子车和打麦场是那时候的标配。
九十年代,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开始在场子里用打麦机脱粒麦子。开始用的是生产队的,后来是几家凑钱买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农村的手扶车、三轮车逐渐多起来了,麦子再也不需要装得高高的,用牛拉着架子车运到麦场里了。很多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打麦机,收麦子的速度比过去提高了几乎一半。
没想到只是几年时间,农村开来了联合收割机,只需要把车开到地里,一会的功夫就变成了一袋袋的麦子。
外出打工或者有工作的年轻人,只在割、晒麦子的这几天开着小车回来一趟,走时留足自家吃的麦子之外,其余的都粜出去变成了现钱。
不需要再割、打麦子或者脱粒麦子了,打麦场上开始长出了青草,好多的人家干脆把打麦场改成了菜园子,有的人家曾经辉煌了上百年的打麦场重又变回了荒山。
六月时节,再回老家,已很难再觅打麦场的踪迹了。
可不是吗?联合收割机多方便呀!院子里、门口都是柏油马路,是不需要打麦场了。
有关上世纪打麦场的回忆,也愈来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