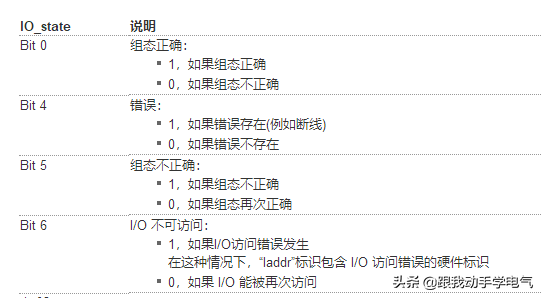旋折莲蓬破绿瓜,
酒杯收起点新茶。
飞蝇不到冰壶净,
时有凉风入齿牙。
——朱淑真《纳凉即事》
转眼夏天又到了,瓜果之属次第上市,街头巷尾,也偶有摆摊以售的小贩或农户,看到这些,不禁想起故乡的脆瓜与甏瓜来。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村前村后的土地全都归了集体,合并为成方成片的大田。靠近村边沟沿,易被鸡刨猪拱的地方,有时候会拿出一些薄田,分给家家户户,名之曰自留地。大田固然须整齐划一,上面号召种植什么,就清一色种上了什么。自留地呢,还稍稍保留了一些个性,可以由着农户自己的性子来。所以,作物里面比较稀罕见的,在这些小块土地上还能遇到。脆瓜与甏瓜,一般就是长在这些自留地里。
不见脆瓜与甏瓜,也有好多年了。如今吾乡的土地,复又以承包之名义归了各家各户,可近来人们所喜欢种的是小麦和玉米,瓜果之属,已由专业农户种植,时移世易,所种也多为时尚的种属,没听说谁家还在种脆瓜与甏瓜;乡间市场上,城中超市里,稍加留意,奇形怪状的瓜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也从来不曾看到过它们。
它们是去了哪儿呢。
为此我曾经遍查植物志书,最后竟然也一无所获。
这一结果让我吃惊,也令我略略不安。我甚至狐疑起来,多少年前,在吾乡的土地上,果真存在过脆瓜与甏瓜这些东西么,我果真曾品尝过清脆多汁的脆瓜与甏瓜么。咬一咬自己的嘴唇,拊一拊自己的大腿,知道自己仍活在人间,而脆瓜与甏瓜的事,当然也不会记错。那么,它们任什么就双双约定,一起消失了呢。
其实,此类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乡间的作物里,大宗的比如棉花,以前那是种遍了村前村后,河南河北的啊,如今它们又去了哪里。零星的,如黍子与稷子,如大麦与高粱,不也难得一见了吗。物种的选育,与日俱新,种植品类的更迭,也日新月异,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相时而动,实也无可厚非。于是,脆瓜与甏瓜,也就被洋香瓜啊、碧玉瓜啊等等瓜类所代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于这些不再被种植的物种,人们习惯使用一个词,叫做淘汰。这觉得这个词下得实在孟浪,有些冷酷无情。物种之有无,乃积千万年自然之力所成,人力之操作,基因之转移,或可得逞于一时,终不可以得势任性,没轻没重,说一些薄情寡义的话,做些没轻没重的事。否则,为什么今天人们又屡言发掘呢。发掘何谓,不就是将迷失了的东西再寻找回来么。
这个最像甏瓜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年艰难窘迫的乡村生活中,脆瓜可能属于那种硕果仅存的闲品。换句话说,在以果腹为唯一人生目标的漫长岁月里,脆瓜与甏瓜似乎仍然是当做水果来种植的:脆瓜一般是不可以做菜的,记得某夏日清晨,实在无物可以佐饭时,先母也曾经将脆瓜拿来切片,撒盐凉拌了吃,那也是一种凑合。其脆松如此,触牙而碎,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脆瓜之所用,也就是摘回来湃在井水之中,赤日炎炎的中午从田里回来,洗出一个,啃几口解渴,最为当行。不过藉此可见,即使饥馑连年,人们也仍然保留了那么一点点对闲适之物的留恋,这也能让人心里生出一点点温馨之意。
吾家自留地距水井最近的,是一块小小的刀把地。先祖父与家父有时就在这里种植脆瓜。
脆瓜之秧,恂恂焉,萃萃焉,并不特别鲜亮,叶子厚纸质,浅三裂或五裂,不结瓜时,与甜瓜、越瓜之叶秧,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待到长出五六片叶子,孽枝旁出,开始开花结蒂时,才渐渐有了区分。脆瓜之形,若青色小棒棰。尾巴稍细而圆,前端稍粗而形长,长大后体有微棱。其着花之时,雏形已具,待渐渐长大,青碧湿润,带着一身的细绒毛,看去真若婴儿之肌肤。待其长成,绒毛脱落,青色渐褪,也就洁白如玉,仪表堂堂了。脆瓜一名,得之其质地,极松极脆,含水真多,一瓜在手,不慎落地,立即粉身碎骨了。所以是最为合用的解渴去暑之品。老了的脆瓜我也见过,那是留作瓜种的,几乎长到净园拔藤。老脆瓜形制巨大,洁白如雪,尾巴虽仍是圆的,前头却已经条棱耸起,如壮夫手臂上的筋脉,昭示着巨大的张力。这时的脆瓜仍然很脆,仍然多水,仍然可口。有时候被叫去吃瓜种,就是吃这种东西,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将种子留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留种的脆瓜,居然个个都有了点儿甜味。
甏瓜顾名思义,其形浑圆如甏。形若蛤蟆酥甜瓜,不同处在于甜瓜往往前丰后削,甏瓜则两端匀称,更兼其上无黑点,瓜皮也青碧近乎透明。微有纵纹,更若碧玉。平时笼统地说,脆瓜与甏瓜,都可叫做脆瓜,必特意点出时,才叫一声甏瓜。论脆度,甏瓜不及脆瓜,论水分,好像也无遑多让。甏瓜的皮稍为紧致,但更薄,其中瓜穰满满,鲜翠欲滴,吃起来也是非常解渴的。
其实,脆瓜也不是绝对不能做菜。当然,我说的是做咸菜。夏末之时,瓜蔓老去,是所谓拔瓜园拆戏台的时候。此时秧子上还有一些小瓜未及长成,如杀鸡取出的鸡卵,大大小小,食之不能盈口,弃之又未免可惜。于是一一摘下来,堆在一边。家母的做法是,将小崽们一一洗净,置入咸菜缸中。秋冬之季,放学回家,肚子咕咕直叫时,搬一块粗面饼子,捞一只嫩绿小渍瓜,那也是一时的绝配了。前些日子与孙石强先生相晤,说起当年旧事,某次在我家,夜深无以下酒,家父即拿出醃渍的小脆瓜,亦是当年困窘日子的一种纪念了。
论说醃渍之用,那还得说甏瓜更为突出。前些年,有朋友常常馈以济宁玉堂酱园的菜品,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所谓包瓜。以圆形瓜剖开,去瓤,其中填以花生、杏仁之属,再缝合起来醃成。品尝一下,果然别有风味。看着有些皱缩的包瓜,隔着酱色,我曾经推断,那该就是吾乡的甏瓜吧。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四有“越瓜”条,说越瓜“形长有直纹,惟汴中产者圆。”越瓜即菜瓜,这汴中所产的圆形越瓜,就与吾乡之甏瓜相差无几了。而脆瓜,也与短一些的越瓜,颇相仿佛。如此,是否可以推断,吾乡之脆瓜与甏瓜,即是越瓜的两个变种,它们与越瓜一样,同属葫芦科(Cucurbitaceae)黄瓜属(Cucumis)植物。植物分类的事,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所以还得请教方家,俟之来者。
菜瓜
;mid=2247484058idx=1sn=3f6e7c29fc7d67fcfc106da981a8edb9scene=1srcid=0806kDX9iO791szi30UtvHcbpass_ticket=SHp96Kxf5U6LhK4mKu6%2B1nq%2BOZQowaDEhlb4q9a1%2BcY%3D#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