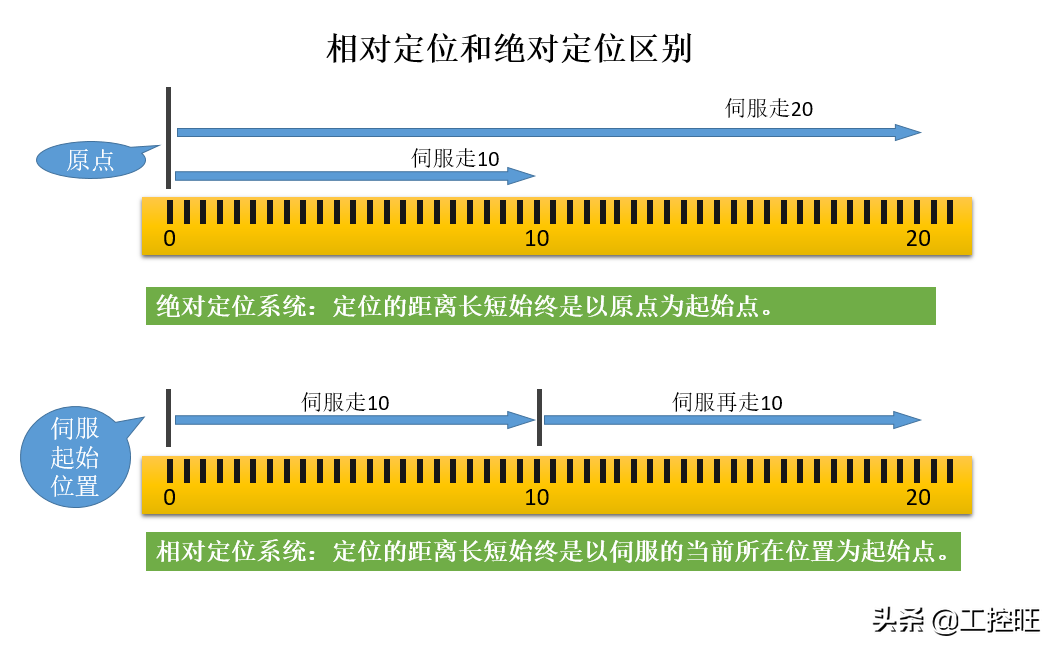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把麦子丢了。
早晨上班路上,早餐摊摆满烧饼油条;中午到快餐店,饭筐里装着包子蒸饺;晚上回家,饭桌上放着馒头面条——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咂摸麦子的滋味,却看不到它的原身。
我是多么想念麦子啊!想念麦苗儿的青草香,想念麦花儿的细白霜,想念青麦仁的清甜,想念烤麦穗的焦黄,还有那麦芒的尖刺,麦穰的暄软,和新麦粒上沾染的阳光——而这些,都像被一阵风刮走了一样,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坐公交车到城郊找。一路是坚硬的马路,路上是连绵的车流,路口是川流的人潮,两边则是高耸的楼房。一路走走停停,走了半天,窗外还是看不到尽头的长路和望不到边际的楼群……
我驾车出城去找。高速公路像一条河流,把我从上游冲进下游,在一片拥堵的车潮里,我终于看见了两岸成垄成行的麦苗。我搁浅在河床上,看着它们在寒风里瑟缩,只能远远地同它们招手……
我乘着火车去找。高铁像一个钟摆,把我从一座城市甩到另一座城市,在风驰电掣的的列车上,我看到了窗外金黄色的麦浪。它们沿着铁路线,像潮水般在身后紧追不舍,又像风卷残云般倏然退去。我困在钟表的盘里,想象着麦浪里涌来的阳光的气息……
我只好回到梦里寻找。
梦里有松软的土地。秋分前后,秋阳和暖,墒情正好。黄牛拉着木犁在前边踱步,农人扶着犁把在后面跟随,犁尖在泥土中欢快地滑行,老人或者妇女挎着筐子,追着犁铧翻开的浪花,一路播撒麦种。
作为孩童的我,也去地里种麦。有时跟在父母身后施肥,将肥料撒进垄沟;有时跑前跑后,送取大人需要的物什;有时在新翻的泥土里侦察,捡拾冬蛰的胖乎乎的豆虫……直到暮色四合,又冷又饿,才随着父母一步一挪回家。
梦里有覆雪的麦田。冬雪过后,村里村外一片雪白。此时麦苗已有大半揸长,入冬来冻得浑身青绿、披头散发,直到大雪为它们覆上一层厚厚的棉被。可北风又来捣乱,扯着被子抻来卷去,从一片雪白中捋出一丛丛翠绿,在阳光下透着刺骨的寒意。
一群孩子从村口跑来,在麦田里互扔雪球,奔跑打闹。跑累了,又蹲下来,一起研究雪地上纵横延伸、细碎杂乱的蹄印。那些细小的印迹让我困惑不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兽,趁夜来踩出这一道道神秘的谜题?
梦到清明踏青,草木吐绿。麦苗比过冬时又窜高了一倍,满眼绿油油的麦田里,散发着甜甜的麦苗香。扫墓归来,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涌进麦地,分成几拨追逐玩耍,在麦苗上打滚,在田野间游荡,在春日里放飞自我。
母亲给我染的红色的煮鸡蛋,还是装在彩线编织的网兜里,挂在我的脖子上。我握紧网兜,跟在大孩子身后,跑得满头大汗,追不上了,就停下来,和别的孩子碰鸡蛋,或者去观察麦垄里攀爬的蜘蛛,看地头水洼里的小鱼,看水面上荡起的波纹,看春风里翩飞的家燕……
梦到芒种时节,满坡麦子变黄。放牛从麦田边走过,使劲拽回把嘴巴伸向麦子的老牛,吆喝着用鞭子驱走撒欢的牛犊,撒一把小石子,轰赶成群飞落的麻雀。热风抽打着麦田,涌来一层层起伏的麦浪,一棵棵青翠的麦杆上,麦叶开始枯了,麦穗青里泛黄。
偷偷揪一穗青麦,放进手掌揉搓。细长的麦芒、粗粝的麦壳,在两手间翻滚。搓掉麦芒麦壳,摊开手一吹,就剩下了青嫩饱满的麦仁,填到嘴里,满口香甜。或者与大孩子一起,随他们采麦穗,看他们生火烧麦,直到麦仁烧熟,飘起阵阵焦香……
梦见捡麦穗。麦收后,麦地一下子空旷起来,只剩下一行行高低错乱的麦茬,像乱糟糟的胡须。挎着篮子,寻宝一样四处搜捡遗漏的麦穗。杂落在麦茬间的,往往是没长全身量的矮麦子,茎细麦穗也短,搓不出几颗麦粒。要是捡到几棵长麦子,或者熟掉头的麦穗,就会捡到宝一样惊喜。奔走寻找半天,常常捡不了半篮子……
梦见割麦。这时我已经长成半个劳力了。直起身,看一垄垄望不到尽头的麦子,千军万马般如潮水涌来,再弯下腰,揽麦、挥镰、收镰——麦秸麦叶重复着撞进怀里,在手臂上锯出火辣辣的吻痕。太阳悬在头顶,汗水滴进土里,变成热气在大地上蒸腾……
梦见打场。赶着牛在打麦场转圈,碌碡吃力地碾过麦秸麦穗,吱吱嘎嘎发表演讲。随后木叉上场,将满场麦穰挑到场外堆成垛。然后迎风扬锨,吹走满身满头的麦糠,剩下一堆麦子,在场中散发迷人的光泽。之后,就是忐忑不安地晒麦看场,祈祷不要下雨,直到颗粒归仓……
——好一场漫长的梦啊!梦里,伴着新麦的欢唱,飘着新面馒头的浓香,还有那一个个新装满的麦缸,和守在缸边的酣睡。梦里,从冬天变为春天,从麦田转向学堂,从村庄走进城市——然后,几十年就过去了。
几十年来,在城市的水泥森林,在高楼的格子间,在人群的潮涌里,在工作的飞转中,像一个抽着鞭子的陀螺晕头转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东飞西飘。等梦醒了,曾经熟识的麦子又不见了。
……
我决定回到老家去找。
可是老家已经大变模样,甚至面目全非了。沿着曾走过无数遍的小路进村,路两旁的老房子包括院墙大多坍塌了,剩下几处未倒的,也没了屋顶或门窗,余下些残垣断壁,倔强而孤独地矗立着。
到处见不到一个人。那些曾在屋院内生活的乡邻不见了;那些带着农具穿村而过的村民不见了;曾经跑来跑去的儿时玩伴的身影不见了;曾经热热闹闹的鸡鸣犬吠、欢声笑语不见了。村庄变成了一个孤寂的荒岛,而我则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到老村旁边的新村。几十栋新旧不一的房屋,大多锁门闭户。九十多岁的老父亲,早早在院门前等着我。除了父亲,新村里的街道上看不到什么人走过。
父亲已经多年不种麦了。犁、耙、木叉、木锨,都没了。窗台上只剩下一把豁牙的镰刀,刀把都快烂脱了。我拿起镰刀比划了几下,发现已经忘记怎么使镰了。
我走到村口。曾经种满麦子的坡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林。林外一方一方半青半黄的麦田,像大地母亲衣服上的补丁。热风吹过,空气中飘来似曾相识的气息。
我走进麦田。一丛一丛矮而粗壮的麦子,举着的长长的麦穗,列队欢迎我。然后,它们散开队形,谦逊地簇拥过来,躬下身低下头,用粗硬的胡须蹭我的手,同我打招呼。
我盯着这些麦子发呆。记忆中曾经那些高高大大的麦子,那些像卫兵一样站得笔直、整齐列队的骄傲的麦子怎么不见了?我咀嚼几粒鼓起肚皮的麦仁。齿颊间又升起淡淡的青麦味道,可是曾经让我心心念念的那种软糯清甜怎么没有了?环顾熟悉而又陌生的麦田,我一时有点儿恍惚……
大哥大嫂还种着麦。大哥说,村里种地的都上了年纪,不过种麦不受罪了,机耕机种,机器打药机器收,“收割机割了麦秸,在地里就粉碎还田,还能脱粒烘干,就是机器割不干净,撇下不少麦穗,都没人捡了”。
大嫂说,这些年总觉得麦子变了,自己捞麦自己磨面,蒸出来的馒头也没有以前的香味了。
——自打离开家,我就没有尝到过儿时的那种麦香。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吃的面粉,它不是家乡种的麦子磨出的啊!没想到多年来,老家土生土长的麦子味道也变了。
那么,小时候那些散发着迷人香味的麦子,那些曾经让我醒着梦着想念的麦子,都去哪儿了?
不管怎么样,我想,等收了新麦,我要带一些回城。我要把它们种在楼下,或者种在阳台上,看着它们生长。
这次,我要陪着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