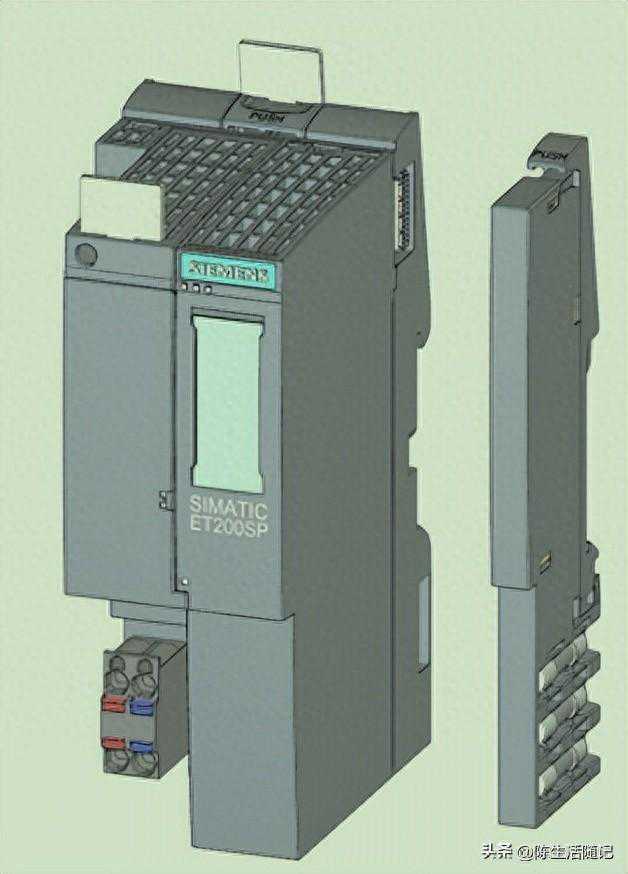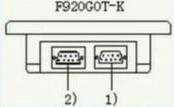五月的关中平原又泛起金浪,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里,麦田被收割回家。
"麦子未熟,切莫开镰。"这是村里周叔常说的,一位老麦客的执拗,也藏着一代人对麦收季最鲜活的记忆。
01
背着镰刀走天涯的"麦海游牧人"
上世纪80年代的陇东黄土高原,四月还泛着春寒,老周就开始磨他的月牙镰。刀刃在石板上发出"沙沙"声,妻子会往水里撒把盐:"淬了盐水的刀,割麦时不粘麦浆。"
这把磨了三年的镰刀,木柄包浆发亮,刀头缺角处是去年在临潼割倒伏麦时崩的口——每个麦客的镰刀都像老伙计,带着各地麦场的印记。
当关中平原的小麦开始勾头,甘肃、宁夏的麦客就沿着西兰公路往东涌。他们背着蓝布包袱,里面装着换洗衣物、打火石和半块肥皂,脚蹬露趾的条绒布鞋,布鞋帮子用铁丝加固过,能经得起十几天的步行。
老周记得1985年那次,他和同村十几个汉子组成"麦客班",步行三天到宝鸡时,鞋底子都磨穿了,索性光脚走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脚底的血泡渗进沙粒,疼得龇牙咧嘴却舍不得歇——怕误了潼关第一茬麦子的"龙口期"。
麦客的营生讲究"赶场",像候鸟追着麦熟的节奏迁徙。陇南的麦子先熟,他们就从徽县开始;接着是关中平原,从宝鸡一路向东割到潼关;等豫东小麦泛黄,他们又顺着陇海线往东赶。
02
弯腰是与土地最亲密的对话
天还没透亮,麦客们就戴着草帽下田了。露水打湿的麦秆带着清甜,镰刀切入秸秆时发出"咔嗒"声,手腕轻轻一翻,麦子就整整齐齐倒向左侧,码成半人高的麦垛。
老周割麦时腰弯成弓,一天下来能割三亩地。割麦讲究"三稳":脚稳、手稳、腰稳,脚底要像钉了桩,手起刀落要顺着麦秆的长势,腰不能贪快猛地直起来,不然容易闪着。
晌午头是麦客最惬意的时候。东家会送来搪瓷盆装的油泼面,辣子面在滚油里"滋啦"作响,蒜香混着麦香扑鼻。
麦客们围坐在树荫下,搪瓷缸里的凉开水"咕咚咕咚"灌进喉咙,汗湿的蓝布衫搭在肩上,脊梁骨上的汗渍画出深浅不一的地图。
傍晚收工后,麦客们喜欢聚在打谷场聊天。月光下,有人用麦秆编蚂蚱笼子,指尖翻飞间,草茎就变成精巧的六边形笼子,笼顶还留个小活门。这些带着麦香的礼物,让东家的孩子记住了这些黑瘦的外乡人,多年后想起,眼前还会浮现那个蹲在草垛旁编笼子的身影。
03
麦客江湖的过命交情
这种朴素的情谊,在机械化收割的时代再难见到——如今机手们开着收割机到地头,微信转账后就匆匆赶往下一家。
麦客之间也有不成文的规矩。遇见落单的麦客,同行会主动分些口粮;遇到地界纠纷,年长的"麦客头"会带着大家评理。
1988年在华阴,当地混混想收"过路费",三十多个麦客攥着镰刀围成圈,刀把在地上磕出"咚咚"声:"我们割的是辛苦钱,要抢就从我们身上跨过去。"
最后混混们退了,外乡人们在外抱团取暖。
千禧年后,联合收割机像金色的潮水漫过麦田。当收割机的履带碾过曾经的麦客之路,那些关于镰刀、草帽、蚂蚱笼子的故事,都沉淀在一代人的乡愁里。
那些在麦浪里讨生活的人,教会我们敬畏土地,也教会我们在迁徙中守望温情。如今麦子依旧金黄,只是田埂上再也等不来那群背着镰刀的人——他们的故事,该由我们慢慢讲给下一代听。